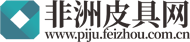阿信今天推荐的书,相信看过标题的你都知道了,是马伯庸的书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但这部作品与马伯庸的其他亦庄亦谐之作相比,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他在 写作上的一次新的尝试。
这本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 《草原动物园》 ,打开了马伯庸文学写作的另一种可能。
故事的核心源自马伯庸家乡赤峰当地的古老传说,但是在他肆意的想象力的基础上,又魔幻地融入了许多非现实的因素:懂动物语言的男孩儿小满、可以盗梦的少女萨仁乌云、月夜成为狼变的马王庙的人……
这种亦真亦幻的写作方法,构建了一个想象力喷发的东方奇幻故事。
有些事情,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这是命中注定
清朝晚期,一个 外国传教士,想在赤峰草原上建一个动物园。
火车、小汽车全没有,更没有水路,自己走这段路就够费劲的了,传教士还要带着动物一起走,连教会都发飙了:
你到底是去建动物园还是传教去了?能不能靠点儿谱?
教士还是特坚持,带着一头大象、一只狮子、一对虎纹马、五只狒狒、一条蟒蛇和一只虎皮鹦鹉 上路了。
要说这几只动物的来历也挺惨的,本来好好地待在 北京唯一一座动物园(万牲园) 里,好吃好喝的被伺候着,谁料想清朝廷穷了,也养不起它们了。
几个动物园的德国保育员一琢磨:估计这动物园要倒闭,咱还是偷偷卖点园里的动物,搞点钱买船票回老家吧。
传教士在报纸上看到售卖动物的消息,眼睛亮了!
他内心的想法大致如下:
这年头,向中国人传教太难了,老套路不行那就想点儿新鲜的,居住在内蒙赤峰的人肯定没见过北京的这些稀奇动物,在那里建一个动物园,先把好奇群众拢一块儿,今后传教也就方便了。
想起来简单但 行动起来才知道有多艰难。
从北京到赤峰,这一路可真不容易。本来走官道,虽然慢点但很靠谱,动物们的食量大,几十斤肉几十斤青草的咔咔吃,沿途没有居民的补给,肯定走不了。
可惜车夫打了歪主意,想走个近道,顺便捞点药材拿回北京卖。穿过草原时,遇见最穷凶极恶的土匪,一群车夫全都被杀死。传教士跳进海泡子(直径大约20多米的塌陷大坑,积满了雨水)里,差点儿没被青草和绿苔给闷死,侥幸捡了条命......
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赤峰,资金有限, 动物园和教堂只能挑一个建 ,思量半天,传教士还是建了动物园,至少让动物有个住的地方。
而 教堂,可以先建在心里。
当地民风虽然淳朴,但人们还是很容易做墙头草,一会儿好奇去参观动物园,一会儿又觉得这些动物是“邪兽”,不祥。
在一次次莫名的谣言后,有人认定这个“动物园”是不祥之地,是邪魅之境,连后来突然出现的守园人也可能是蟒蛇化成的人形。
于是, 动物园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。
阿信第一次读完这个故事,觉得就跟寓言的天方夜谭似的。
但细细揣摩起来,处处都透露着心酸。
为啥这个 传教士一定拼了老命也要去赤峰建动物园?
还未动身前,当他第一次在地图上看到“赤峰”这两个字,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样奇妙的景象:一座红如火焰的山峰拔地而起,冲破云雾,直刺苍穹。
这场景莫名又神秘, 他竟和中国一个陌生的地名就有着这样强烈的共鸣。
“有些事情,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,这是命中注定。赤峰就在那儿,它是我和这些动物的应许之地。我别无选择,只能遵从意旨。”
信仰的力量,支撑了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人生地不熟的中国,做出了这么一件震惊天下的事。
他对整个世界从未厌倦,也从未长大
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,阿信觉得最感人的,就是 传教士和灵魂伴侣——那头名叫万福的小母象之间的感情。
传教士第一次看见万福,是在北京动物园里。那时候的万福,瘦骨嶙峋,孤独地站在一块巨岩之下。
深陷的双目黯淡无光,连萦绕四周的绿豆蝇都不能让眼珠转动一下。她的右后腿上拴着一条锈迹斑斑的粗大铁链,链条已经紧紧勒入皮肉,边缘结起了厚厚的疤茧,链子的另外一端缠绕在一根木桩子上。
从出生到现在,万福从没离开过动物园,它很胆小。但它似乎 和传教士之间有着某种感应 ,她顺从的跟随他上路,从一开始卸掉链子时,一瘸一拐不敢迈步到后来钉上铁掌,健步如飞, 万福一直在改变,变得更自信,更活泼。
路上遇到一条河,羞涩的万福戏水,慢慢地开始清洗身体,这时传教士才发现,万福居然是头神圣的白象,之前的一身灰只是因为之前万福从没洗过澡而结出的污垢罢了。
这个桥段的隐喻不言而喻,读到自会心领神会。
夕阳下,洗净身体的万福,温顺极了。那一幕也神圣极了,传教士心中默念, 万福就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信徒。
读完这本书,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“传教士怎么这么固执”的印象,他的所有行为,在常人看来,都太奇怪、太任性了——不听劝、一意孤行。
他不愿意像其他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,做些所谓“入乡随俗”的勾当,他只是一直坚持,用自己能够理解并赞同的方式,去完成他的使命。
但其实,书中处处都在暗示,他所做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决定,都是 对信仰的坚持。
作者是这样形容他的,“一个人可以固执,也可以异想天开,当这两种特质合并在一起后,他就会变成一团跳跃的火、一台上足了气的蒸汽机。”
但其实, 他对整个世界从未厌倦,也从未长大。 或许对这位传教士来说,信仰就是永葆对世界的好奇吧。
“总有人披荆斩棘,心向草原,才成为自己。”
是奇幻故事,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征途
《草原动物园》于2017年首次出版后,已陆续出版了韩语版、西班牙语版等。
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这样评价这本书:
用深入浅出、大开脑洞的方式写历史,善于发现大的历史叙事中暗藏的细节,是马伯庸作品最鲜明的特色之一。 每写一部历史小说前,马伯庸都力求将功课做足。
比如为写这部《草原动物园》,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内蒙古赤峰,搜罗那里的传统民间故事,找来关于清末的文献和论文,大到赤峰城的格局、官府的职位,小到当时报纸的名称,一一敲定。
马伯庸说这本书,是他回到故乡的方式:
赤峰是我的故乡,我在这里长大。故乡对我来说,是一个充满乡愁和魔幻的童话。
本次再版,由马伯庸进行了详细修订,书封也进行了重新设计,新版视觉中心是 具有狂欢感的元素 ,并勾勒了金黄色版画风格的四周元素,又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进行搭配,瑰丽的想象力喷薄欲出。
这场动物园的迁移之旅,对我们而言也是 每个人坚守心之所向的现实经历。
在阅读中看到时风世情、人与动物的神奇关系,以及人对自我的探索与救赎。
在险途中,看到人心繁复、信仰的复杂性和虚实世界的辩证性。